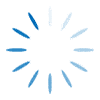贴上来的鼻尖和嘴唇微凉,舌头却滚烫,带着新鲜浓郁的薄荷气味,沉沉压入口腔,专横又凶猛。
夏棠很想把他推出去,喉咙里溢出低低的哼鸣,手腕被他握着越发吃痛,浑身紧绷想挣扎出一点响动,但被钳制得极死。
她可以张嘴咬他,就像以前做过的一样,比那次更恶狠狠地、攒足力气,让血腥味蔓延口腔。
但她偏偏犹豫了一下。
吻里薄荷的凉意就像岩浆底下藏着的冰霜,夏棠空着的那只手紧紧掐着他的胳膊,用的是最大的力道,这个人却毫无觉察一样只管吻她。鮜續zнàńɡ擳噈至リ:i5 2y zw.c om
舌尖深入,一手握着手腕,另一只手捧着她的一边脸颊,让她的头颅不能动弹,暗沉沉的影子将她整个盖住。
咬他就好像把一只冰天雪地里无家可归的流浪狗踹出屋檐下。
就在犹豫的一小下,夏棠开始缺氧。
忽然有哐当的一声响,是她推到了旁边的书桌,桌上的东西开始接二连三往下掉,她的课本,练习册,然后是清脆的噼啪声。
林清让送她的香水瓶从桌上滑下来,干脆利落地在地板上摔成数块,强烈的香气瞬间弥漫,就像一颗芳香炸弹。
她咬了陆霄一口。
血腥味伴随着浓郁的橙香,本来是清淡又纤巧的香气,这时候却过分的浓烈。
夏棠的手腕得到了自由,她终于能喘上气,大口大口呼吸着甜腻的香气。
陆霄站在她面前,被咬破的唇瓣渗出殷红的血迹,他额前的头发变得很乱,在黑风衣里像只高大狼狈的吸血鬼,侧头看了一眼地板上摔碎的香水瓶。
半透明的液体在地板上缓慢流淌,散发出熟悉的香气。
让人分外轻易就能知道,这瓶香水是来自于谁。
他转回头,夏棠正在下意识用手擦去唇上的血腥气,背靠墙扶着书桌的样子透着些无助似的惊慌。
陆霄后退几步,远离她,香水流到他的脚底,碎玻璃片咔嚓作响。
这时候他的眼里没有了那些暴戾残忍的部分,在几步之外定定看着她,目光空泛又带着点自卫式的倨傲,仿佛是一只真正的跑出屋子的丧家之犬。
“喂,你……”夏棠试着发声。
嗓子忽然有些哑,说到一半就失去了声响,弯着腰干咳两声。
她也没想咬他的。
更多是受到了惊吓。
陆霄绷着脸颊盯着她,染血的嘴唇动了动,最终还是没有说出那句可能的抱歉,转身拉开房门离开。
背影又沉又冷硬。
只有夏棠独自在又变得乱七八糟的房间里,慢慢地背靠墙壁蹲下来,力气好像都从指尖被抽空,她弯着腰把额头抵在膝盖上。
到这里就是真的结束。
她想。
第二天夏棠是自己拖着行李箱,从大宅出发,走过坡道去坐公交,坐完公交再穿过大半个校园,坐电梯到自己宿舍所在的楼层。
管家本来要司机送她,但夏棠摇了摇头说可以自己过去。
地下车库里的车都属于陆霄,无论哪一辆,在她眼里都闪闪发光得显眼。
她宁愿自己走过去。
临行前,她爸妈还有些担心昨晚的事。她很明显是和陆霄吵了一架,这种事小时候也常出现,但最近几年已经变得格外罕见。
大人的吵架和小孩子的矛盾可是两码事。
夏棠只说没事,她撇了撇嘴唇,又说:“他也是,过一阵就会好了。”
虽然这一阵可能要好几个月,甚至也许是半年,但再怎么样也不会超过一年。
因为那时候他早就已经去了国外。
夏棠是住过宿的,对入住宿舍这种事熟门熟路。
她的舍友除了李子沫和赵悦月,另一个也是拿着奖学金专心读书的女生。
大家都是好相处的人,周日晚上赵悦月还买了低度的罐装果酒回来,作为她搬进宿舍的欢迎。
大家把罐子碰在一起,当当的声音,昭示着宿舍生活将有一个良好开端。
夏末秋初的天气反反复复,到下一周,温度又忽然变得酷热难当,阳光灿烂的直射,照着深绿的叶片。
本来以为就要这么老死不相往来,才过一周,夏棠又在学校里见到了陆霄。
对于这件事,校园论坛里罕见的安静如鸡,所以当她冷不丁抬头望见时,感觉耳边安静,心跳一空。
那家伙正站在走廊那一侧尽头。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