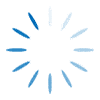陆霄显然是刚回到家,进门时连外套都没有脱下,深色的长风衣有着剪裁硬朗的肩线,下摆笔直向下,他的眉眼同样凛凛地向下。
垂眼睨着她,轻抬起下颌,矜傲地开口:“卫川生说,你一直在问他找我。”
“所以,谈谈吧。”
面前男生的眼睛黑如点漆,额角碎发轻搭,也许是因为光线问题,五官看着比平时还要深。
在谎报军情上,卫川生是有一套的。
夏棠腹诽。
背后的走廊随时可能有人经过,想了想她还是先开口:“要不要去……”
“不用。”陆霄一个人挡住门口,声线凉凉的欠缺起伏,“他们不敢过来。”
鬼知道他怎么跟其他人说的。
夏棠的手在口袋里攥了下宝石项链,深吸口气,而后抬起眼,看着他开口:“上次你说的……那些……是认真的?”
问题出口后,陆霄下意识压了下眉梢,他轻抿唇线盯着她的脸,静默了几秒。
夏棠微微屏住呼吸,仰头注视他的眼睛,捏着手指,在这一刻等待他否认。
否认了就一切都好了。大家各退一步,打着哈哈说什么喜欢,只是一时冲动顺口说出来的,都被这么无视了,那点喜欢早该破裂了。
“是。”他说,破罐子破摔似的语气,眼梢垂下,“我说喜欢你,全部是真的。”
语气那么别扭,话语和视线却直白如刀刃,一时间像是要戳穿谁的心脏。
夏棠和他对视不到一秒,就仓促收回视线,看着走廊上的地砖。
出口的声音变低,本该很有气势的反问成了窃窃的抱怨:“但是你又没告诉过我啊?……这种事不应该一开始就说吗?”
“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了。”陆霄淡声说,“在第一次的时候。”
夏棠被堵住。
她想起那个阴云密布的傍晚,陆霄卷起袖口,站在乌沉的天宇下,问她怎么想那晚的事。
怎么想他们之间的事。
“就算这样,你就没觉得不对劲么?”她重新抬起头,看着他的眼睛,“无论怎么看,我们这样也不像是正常恋爱啊。”
正常恋爱不会规定着时间和次数上床,不会没有表白,没有约会,没有甜言蜜语,在牵手之前就先学会做爱。
正常恋爱应该是在袖子底下偷偷牵着手,晚上偷偷地打电话聊上几个钟头,周末一起去游乐园,戴着很蠢的头箍合照。
那才是普通情侣的样子。
陆霄站在她面前,像被这些话语刺中似的,唇角线条绷得越发紧,眼里就像楼道里老旧的钨丝灯泡,再怎么努力发光也隔着一层炭黑的尘雾。
“我是不知道正常恋爱是什么样子的。”他说,“我以为我们这样就是。”
放在往常他早该发怒地走掉了,可现在他都还没走,像要证明什么似的脊背仍然笔挺。柔和的暖色灯安静地亮着,照着男生像照着一棵被雨淋过的云杉树。
身后长廊空荡,仿佛有偌大的寥落都要那里涌进来。
长在城堡里的大少爷不知道什么叫正常恋爱。
他从没学过,没见到过,没人教过他。
他只知道约会要去电影院,周末要带喜欢的女孩去看流星,生日不能够忘记送礼物。他练了半个月的钢琴,可是最后又换成看流星雨。
夏棠垂眼看着走廊上的地砖,心想这家伙到现在也不知道装傻的艺术。
胸口一片潮湿,就像被纠缠在绵长的雨季,凉风吹着细雨沙沙而下。一大团棉花填满胸腔,整颗心脏闷闷得呼吸不透。
这个错误实在是耽误太久了。
项链在口袋里被握得温热发烫,她静了很久才开口:
“……其实也没差太多么……”
鞋尖磨蹭着地面,让语调尽量无所谓:“世界上也是有很多人,是和我们一样谈恋爱的——”
归根结底,只是一点小小的,还来得及纠正的。
认知偏差而已。
她仰起头,看着他的眼睛:“不如就当做我们,从现在开始分手好了。”
今夜没有下雨,但仿佛有雷声自寂静处响起,轰隆隆的骤雨落下。
陆霄站在门口,视线一动不动地看着她。
夏棠一鼓作气地继续:
“……你看,我之后这一年要准备考试,你也马上要去国外。趁现在分手,就是最好的时机。”
她抬头看着他,一只手仍放在口袋里,脚尖无意识点着地板的纹路,棕色的眼珠在光下有如琥珀,分明又澄澈:“要是……你觉得被人拒绝很丢脸,就当做是你把我甩掉的好了。”
夏棠的确是很真心地觉得这是条好提议。
像这种又麻烦又耗时又注定没有结果的关系,尽早结束才是最正确的做法。
那些喜欢啊,恋爱啊之类的感情,只是青春期躁动不安里的错觉而已。
很快会被忘掉的。
她抬起手肘正要拿出口袋里的项链,耳边轰然响了一声。
夏棠条件反射抖了下,缩起脖子。
手臂横在门框上,陆霄下颌收紧,眼睛无声盯着她。
这回他是真的生气了,五官和棱角愈发显得锋利,光线在脸上交错。
他往前一步, 距离拉近,夏棠下意识后腿,立在那里的行李箱被小腿撞了下,塞满的箱子闷声倒地。
卡通贴纸的那一面朝上,没有嘴巴的hello kitty正大大睁着眼睛。
陆霄收回视线,看向她。
夏棠绷着脊背,开口解释:“那个……就是节省时间……我打算搬去住宿舍。”
她的鼻尖几乎挨着面前人的胸口,靠得太近,外套里带着的冷冽气息扑面而来,是很熟悉,很熟悉的气味。
说话时温热的胸膛颤动,声音却压着越绷越紧的寒意。
“要是我没有回来,”他问,“要是我今天没有见到你,你就要直接搬走吗?”
夏棠仰头:“我只是——”
话语戛然而止,因为陆霄已经握住她的手腕。
他把那只箱子踢到墙边,将人拽进门内,压在墙壁上,眼瞳里铅黑的云团聚集,仿佛暴风雨降临前的海面。
随时会大雨倾盆……似的。
夏棠屏着呼吸仰头望着他,心跳声鼓噪,汗毛竖起,只有睫毛随身体轻轻地发着颤,透露出一点下意识的慌张。
睫毛像结了一层汗水似的发沉,她靠着墙,眨下眼,想把那层不存在的水珠眨掉。他们的脸贴得很近,鼻尖靠着鼻尖,是只要一抬头就能贴上嘴唇的距离。
面前这个人一直都是个脾气糟糕、无法无天的家伙。
他生气的时候是真的可以踩断人骨头的暴戾,只是因为相处太久,时常让人忘了这件事。
夏棠的手腕被用力攥住,投来的视线就跟握在腕骨上的力道一样重。她能从他的眼睛里看见自己的倒影。
光线越过他悬直的鼻梁,一寸一寸涂抹过脸颊,却没有在眼睛里停留。他的眼睛里满是刺,但刺到的只有他自己。
手腕上的力度慢慢地松开来,陆霄抿唇盯着她,声音出乎意料的低:
“为什么你可以说的那么简单。”他问,“我又算什么?”
他的眼廓线条凹下去,声音就像正踩着谁的骨头说出来的,像是别人的骨头,也像是他自己的骨头。
夏棠觉得自己的心脏像被人捏住,密不透风地握着,怎么呼吸都穿不透。
周围安静,她说不出话,不小心撞到书桌,东西接二连三地掉下去,她的课本,练习册,还有林清让送她的香水。
随着清脆的噼啪声,玻璃瓶在地板上摔成数块,就像引爆了一颗芳香炸弹,本来应该清淡纤巧的香气弥漫得过分浓烈。
那是她身上的香气,也是林清让身上的香气。
半透明的液体在地板上缓慢流淌,陆霄侧头看了一眼地板上摔碎的香水瓶,垂着眼,心里想“哦”。
他知道的。
就像马戏团里的新手杂技演员想讨女孩欢心,可女孩其实并没看见他,即使偶尔发笑,也从来不是因为演员蹩脚的表演。
那女孩从来一无所知。
他后退几步,远离她,香水流到他的脚底,碎玻璃片被咔嚓踩成粉末。
这时候他的眼里没有了那些暴戾残忍的部分,眼瞳里的云团坍塌,没有电闪雷鸣和暴风雨,剩下来的只是那一点最后自卫式的倨傲,仿佛真正是一只失去住所的流浪犬。
最后也什么都没说,转身拉开房门离开。
只有夏棠独自在又变得乱七八糟的房间里,忽然想起什么,赶快从碎玻璃片里抢救出自己的练习册,手指被碎片划破,冒出殷红的血珠。
香水沾湿了课本的一角,她一边含住手指,一边把书拎起来抖了抖。
力气突然间好像都从指尖被抽空,她抱着书背靠墙壁慢慢地蹲下来,弯着腰把额头抵在膝盖上,心里告诉自己说,总会好的。
这才是正确的做法。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