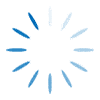“我这有个好消息,我可能找着薛家大郎要下手的原因了。”
尽管如此说了,十六却挨住了何冲的软磨硬泡,直等着回了房间,才开了金口。
“说呀,你究竟发现什么了?”
何冲早已不耐,恨不得给十六脑袋上钻个洞,自己直接往里看个清楚。
十六却不急不慢地坐了下,如牛饮水猛灌了半壶茶水才停,有些粗直地抹了把嘴,才缓缓说起了缘由。
“今日我远远跟着他,先是去长辈各处请了安,又回了书房温了半日功课,再去了园子里习箭,从园子回来时走的小道,那条廊最是逼仄,路上碰见了薛家姨娘,二人相对而过。”
说到这里,便停了。
留下何冲并着金展,还等着下半截的话,胃口被高高吊起,却没了下文,便如那被引得吃了一半软酪的耗子,被勾得入了彀。
“就这样?”何冲等了半天,脱口而出这句,金展虽是厚道人不好出口,憨厚的黑眼睛里却也有些困惑。
十六却拿眼睛去瞧李玄慈,只见他指尖摩挲着杯缘,原本冰凉的瓷杯都熨上了些暖意,见她看过来,便抬了眼,若有所思道:“相对而过?”
十六仿佛从树洞里挖了蜜的小狗熊一般,忍不住偷着抿爪子,偏还要在面上按捺住,只一双眼睛弯弯的,瞧着便让人开心。
“对,相,对,而,过。”她一字一句地强调起来。
这下,其他二人也品摸出些味儿来,知道了重点放在何处,却仍有些不明白。
“你的意思是,这二人有私?可是有什么逾矩之处?”金展问道,何冲还在旁边忍不住飘着眼睛作出搂搂抱抱的亲密姿态来示范一番。
“不曾,二人便是说话也隔着距离,更别提有什么逾矩的亲密动作了。”十六摇摇头,瞪了眼自己矫揉造作的师兄。
“只是,因那回廊逼仄,二人擦肩而过时,是正面相对着过的。”她补了一句。
金展和何冲两人对视了下,彼此眼中俱是迷茫。
“那又如何,你也说了回廊逼仄,那擦肩时挨得近些,也是难免吧。”金展忍不住说了句。
十六眼里闪过狡黠。
“这便是你们鲁男子见识不足的地方了,一看便是平日里没有什么女人缘,才会这般迟钝。”
“这女子与男子错身而过时,下意识身体便会错向与他相反的方向,极少会有用上身正对着男子的,万一擦着可怎么办。”
“便是寻常男女往来,也会注意,何况是嫡子与小娘这样的尴尬关系,更是要多多避嫌的。”
“言语可以骗人,行动可以遮掩,但细微之处下意识流露出来的东西,是不会说谎的。”
这番话,皆是十六切身体验,她自大了些后,便要缠裹着胸乳,后来还好,刚开始缠时,稍稍一碰就酸疼难忍,跟胃里塞了酸掉牙的杏子一般。
她那时也不太懂男女之别,别的师兄师弟都没有,师父也不许她同别人说,十六只觉得自己像是身上长了疮,藏了脓,心中慌乱却也不敢言语。
自那时起,她便知道自己和师兄弟们都不一样,刚裹胸时,有段时日还曾躬着背、塌着腰走路,与人路过时也多有避让,平日里过了好一阵才算正常起来。
有了那段经历,她便比任何人都更深地体会到了这世间对女子的束缚,生了这样的身体,受着这样私密的罪过,连与人擦肩而过时,都要下意识地将自己藏起来。
这下,金展与何冲才算听明白了。
“你的意思是,他们二人有私,所以才下意识于肢体上流露出这样的亲密,但这这可是逆了伦常的大罪啊!”
这事要是真的,如果露了一点风声,薛翼便算是完了,权贵家的少爷流连花丛不要紧,可与父亲的妾有勾连,还是这么个实质上有一半养育关系的妾,那可真是天大的丑闻。
“如果那薛蛮蛮是窥见了什么,又被他俩所察觉,想杀人灭口便合情合理了。”十六点点头。
“不止。”
李玄慈难得插了一句,眼中含了些意兴阑珊。
“他们敢痛下杀手,怕有一半的原因,是知道我来了之后才起的兴。”
这话的意思,十六在心里头转了下,才明白其中歹毒。
李玄慈身份贵重极了,与皇帝关系更是微妙,且如今他进京之事显是私密,更妙的是,他还恶名在外,如同阎罗降世。
要是他住进来时,出了这样的“意外”,便有两种说法。
一是圣上此刻并不欲发作,那便会极力按下此事,甚至不让深查,不是意外,也成了意外。
二是圣上正欲拿这做伐子,他们便刚好递了刀,不是李玄慈做的,也会成他做的了。
倒是天大的胆子,歹毒的心思,横竖两条路都算计透了。
想透了这一层,连十六这半个苦主都忍不住击节叫一声好。
敢算计到阎王头上,这可真是。
活够本了吧。
更☆多☆章☆节:wo o1 8 . v i p (W oo 1 8 . vi p)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