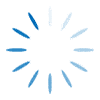*
太傅的年纪比国公还大了,仍孜孜不倦,之乎者也的挂嘴边。
楚王向来不喜周礼,认为六艺中礼教最没用,太傅就不高兴了,二话不说往学宫的门梁上挂上“万般皆下品,惟有读书高。”几个大字。
每个士族踏进学堂,首先就要对这几个字顶礼膜拜。
良芷对楚王的看法深以为然。然而身为一个公主,诗书礼仪她落后几个姐姐百丈远,远得连王后都忧心忡忡。
所以入夏后,良芷就被勒令去学宫上课,还是早课,由太傅单独授学识。
授学的第三日,太傅在台上讲,良芷趴案上听。
“究竟是谁呢……”
她撑着脑袋,动也不动。
那暖春阁的小倌昏迷了几日后,良芷又去寻他,却被告知他只是看上公主美色,又听闻楚宫中多是伶人当男宠,才斗胆想自荐,不料碰上了盗贼一顿搅和,醒来后羞愧难当,已经辞了职回老家去了。
这个说辞,怎么感觉有哪里不对?
良芷盯着前方,连太傅靠近都未曾察觉。
“公主?”
太傅低头一瞧,面色渐渐沉下去。
纸上一句笔记都没有,全是涂鸦和杂乱的墨迹,他痛心疾首直晃头,花白的胡子越扯越掉。
他大声斥道:“公主!”
良芷的笔啪嗒掉了下来,“啊?”
下了早课,良芷唯一的收获就是要抄写国书三十遍。
舒落忍着笑给良芷提书箱和学具,良芷受不了她这模样,打发她先回去备午饭,说这天气热,想吃绿豆粥,叫她别多放太多糖。
舒落见公主心里有事已经几天了,就应了声先回芳兰殿。
偌大的听心湖用水汽带走炎热,一黄衣侍卫正顶着大一倍的盔帽,靠着树桩在绿荫底下打盹,时不时有高一等服饰的步兵巡逻路过,对他懒散的站姿见怪不怪。
与别的侍卫不同,别的守岗人持的是长枪,他手边什么都没有,只有腰间别的一柄薄而窄的长剑。剑鞘虽古,绑的剑穗却极为精致。
耳边细细嗦嗦,他下意识先站直了,再慢慢睁开眼,对上一双杏眼。
这眼带三分好奇,三分兴味,余下几分透亮里倒映出他的窘迫。
他脑袋往左,那双眼睛就不动声色往左边去对,他只能乌龟似地再往右去错开。
对无可对,良芷扑哧一声笑出来。
“我说呢,这小兵怎么这么眼熟,大楚第一剑客,你站这儿跟个木头似的,就脑袋转来转去,做什么呀。”
步文驰梗着脖子,“看不到吗,站岗啊。”
听心湖离议政之地很近,所以看守会比别的宫殿严格的,百步设一岗,一直要排到湖对面的文华殿。
良芷道:“平时叫你进个宫都推三阻四的,我正想过几日出宫找你呢,想不到你自个来了。”
步文驰说:“你以为我想啊,你阿公回了。国公觉得我无所事事,命我来的……你有时间去看看他。”
良芷“嗯”了声,又盯了他一会,总算意识到哪里不对劲。
她仰面捏住步文驰的下巴,用拇指搓了下,没掉色,她问:“你这是站太阳底头晒了多久啊,怎么黑了那么多?”
步文驰别开脸,只说:“因为你们宫里的姑娘们太猛浪了,我不丑些,被看上了,抢进后院可如何是好。”
她忍着笑:“就你?”
良芷承认步文驰有一副好皮相,就是这性子太惹人烦。
“今儿这的水清,你要不要下去,好好照一照你现在这个黑不溜秋的鬼样子。”
步文驰知道瞒不过她,转了语气,“哎,师傅他老人家,突发奇想要研制什么新的易容药,还打包票说一定能洗干净,结果就这样啦。”
他把脸伸过来,“他拿我做试验,管生不管养,阿芙,连你也觉得我丑是不是?”
良芷知道这人容易蹬鼻子上脸,索性不理他。
湖畔的水榭离这里近,接天莲叶无穷碧,荷叶涨池,荷花朵朵饱满,伴着沁人的荷香,顶头又是翠郁的古槐,贪这十足十的幽凉,日晒不到,风轻轻吹。
站在荫蔽下,良芷正想感叹他挑了个好地方,步文驰看着远处,忽然道:
“你们楚宫中居然还有人喜欢穿得那么白,跟去奔丧似的。”
“谁?”
步文驰用下巴点点,良芷顺着望去。
湖对面是文华殿,是楚王平日议政的地方,一个白影徐徐从殿门里出来,同迎门的宫官行了礼,正走上拱桥。
是姚咸。
黑发雪衣,走动时带起衣袂拂开些,身后是金瓦红墙,四周是碧色的水影摇曳,他一身白得醒目,因为这白,使得旁的景和人都要变模糊,独独突出他一个来。
似是感受到了这边的目光,姚咸也遥望过来。
“你认识他?”
良芷否认,“不算吧。”
步文驰眯眼,“撒谎。”
因为姚咸直接往她这边来了。
他一如既往的平静恬淡,面容却比上回见他要苍白得多,好看是好看,总觉得缺了些生气,良芷想或许是因为玉泉不在的缘故。
姚咸行了礼,“公主。”
“怎么就你一个。”
转念想他从文华殿出来,应该是楚王要见他,玉泉不在也正常。
姚咸果然不答,反而微微一笑,温声问:“公主的伤,好些了么。”
良芷下意识摸上脖子,那块地方已经恢复平滑,她笑,“已经好全了,还要多谢公子的药膏,实在好用,我能跟你再讨一罐么?”
姚咸的笑和回答都很有分寸,“公主客气,若还想要,我可以将配方写下来,公主自行遣人去配。”
湖边的风晃动树影,姚咸含笑的模样柔和而无害,却像隔着一层纱,看不透真正的情绪。
而正是这份“看不清”,让他身上有种难以捕捉的迷,这种迷使得所有人都趋之若鹜,他只要目光投向你,你就很难再去看别人,因为他眼里很难有旁人,因为每个人都想自己成为特别,而他能成全这种特别,哪怕是一瞬间的错觉。
良芷点头,“嗯,好。”紧接着便是一阵沉默。
良芷的目光中是带着审视的,连她自己都没意识到。
姚咸垂下漆黑的眼眸,说有事要先告辞,良芷本就同他没话讲,就让他走了。
“不认识他关心你伤好没好?”步文驰盯着姚咸的背影,冷不丁道。
他抱胸站着,“你别同他走太近了,最近楚渊之间不太平,不知道要发生什么,你离他远些。”
良芷说:“我和他本来也不熟。”
“那可不一定,”步文驰耸耸肩,“这张小白脸很难不心动吧?”
良芷:“哈?”
步文驰指了指从旁经过宫婢们。
只要是见着姚咸,无一不侧目偷看的,只是无人上去行礼,在一旁窃窃。
“这几日我听宫人们闲话,听到了些事情,你二姐姐的事传得够广,她这人你也知道,带头欺负人呢,你这人旁的什么都好,就是容易同情心泛滥,你可别脑子一热也往他那处送。”
良芷自动忽略他的话,目光追随着姚咸的背影。
从主道上来了一波人,个个锦衣华服,是别国的质子和几个侯门子弟,是去应楚王的召见。
他们见姚咸迎面而来,顿了顿,彼此之间交换几个眼神后才继续往前,忽然从中有人歪了个方向,斜身朝姚咸狠撞过去。
姚咸直接被撞倒在地。
见人倒了,几个人嬉笑着也不道歉,就看戏似的看地上的人。
狼狈是没有的,什么都没有,姚咸毫无反应,也不看他们,用手撑起地面,慢慢站了起来,然后拂手掸去身上的灰尘。
他的反应出乎他们的意料,几个人面色挂不住。
为首的人说了句:“不知道在高贵什么!”
姚咸是听见了的,他抬起头,眉目间自带一种奇异的沉静和从容,与那人对视一眼。
那人只觉得这了然的目光能将他看穿,莫名生出种被戳穿的羞怒,那怒爬上脸,他张口还想说什么,有人撞了他肩一下。
他不耐地转头,公主正目光灼灼地注视着。
他与同伴面面相觑,匆匆行了礼,快步走开,经过公主也自动绕远了走。
嘴脸真是难看。
良芷想着,正要走过去,步文驰捉住她的手腕,说别忙,你看。
一个宫婢装扮的人提着一匣子走过来,切切双手奉起,要塞给姚咸,姚咸倒退一步,信手搭在匣子的手柄之上,往前一拂,意思就是婉拒了。
那宫婢又坚持几下,姚咸还是不受,施施然行了礼,侧开她兀自走了。
步文驰哼了一声,“还算有点骨气。”
那宫婢站在原地,低头抱着匣子,有些不知所措。
“喂,你过来。”
良芷招招手,那婢女迟疑片刻,走了过去。
婢女行到跟前,刚行了个礼,便听见公主厉声道:“你是哪个宫的人,楚宫中私相授受,是要受刑的,你不知道吗?”
婢女扑通一声跪下,也不敢自报家门,只是打开怀里的匣子。
匣子只有一层,用绢布垫着,上头排放整齐是瓷瓶,一个个用素纸贴好,朱砂,天青,黛绿……
都是颜料,一旁还摆了各个尺码的笔豪和作画器具,还有一片金叶子,但只有这一片。
婢女低头解释道:“我家主子得过公子咸的画,甚是喜欢,想再求,公子推脱说颜料用尽了,没余钱入新的,打听了才知道,是二公主放出话来,说谁都不许买公子的画。知道公子在宫中受苛待,我家主子才央我送来的,没有公主你想的意思。”
“二公主只说不让他卖画?公子咸的画很值钱?”
“值钱的,但是二公主说这种行为要败了画师的脸面,觉得楚国的画技名声落到旁的小国头上不好,还有其他的……公主你应当能猜到。”
良芷点点头,“嗯,知道了,我不说就是了,你走吧。”
婢女应了,合好匣子,行了礼后走了。
步文驰摸摸下巴,“想不到多年不见湘兰,她性子还是这般难对付。”
良芷斜了他一眼,“喂,她好歹是我姐姐。”
步文驰耸耸肩。
良芷忽然想到了什么,“对了,那日我叫你查的人呢?”
提到这事,步文驰头疼起来,说我的公主啊,你叫我查,也得告诉我线索啊。
“他长啥样,不知道。身高,声线,年纪,总得占一样吧,啥都没有,你叫我查什么。”
“那银针呢?”
“又没毒,那种针满大街都是,就光你芳兰殿里,都能搜刮出八百根来,更别说那整个王都了。”
良芷:“放屁!我殿里最多八根。”
步文驰:“……”
芳兰殿门口多了一大堆东西,舒落在旁用册子一一清点,良芷问了才知道,是国公两日前回了王都,这些都是国公从中原带来的礼物。
良芷看了一会,盯着两扇极为朴素的屏风不动。
舒落见了,也头疼,说这屏风的雕花不错,就是太素了,放在芳兰殿哪哪儿都不合适。
良芷想了想,有了主意,遣了两个人,说要将这两个屏风抬去斋清宫。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